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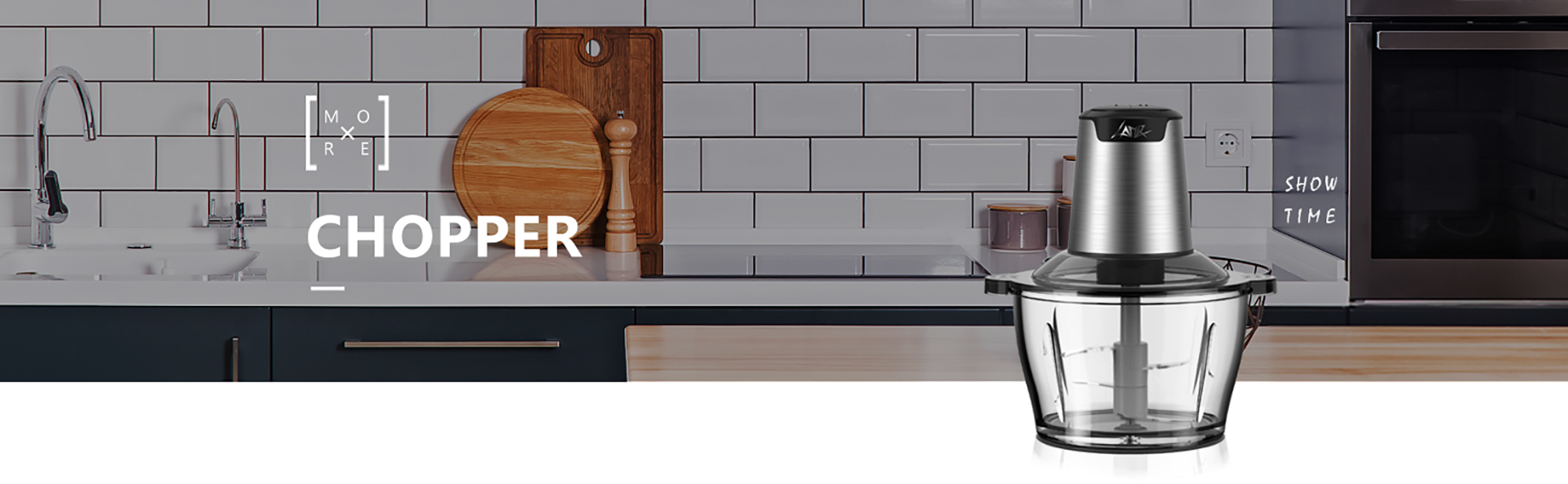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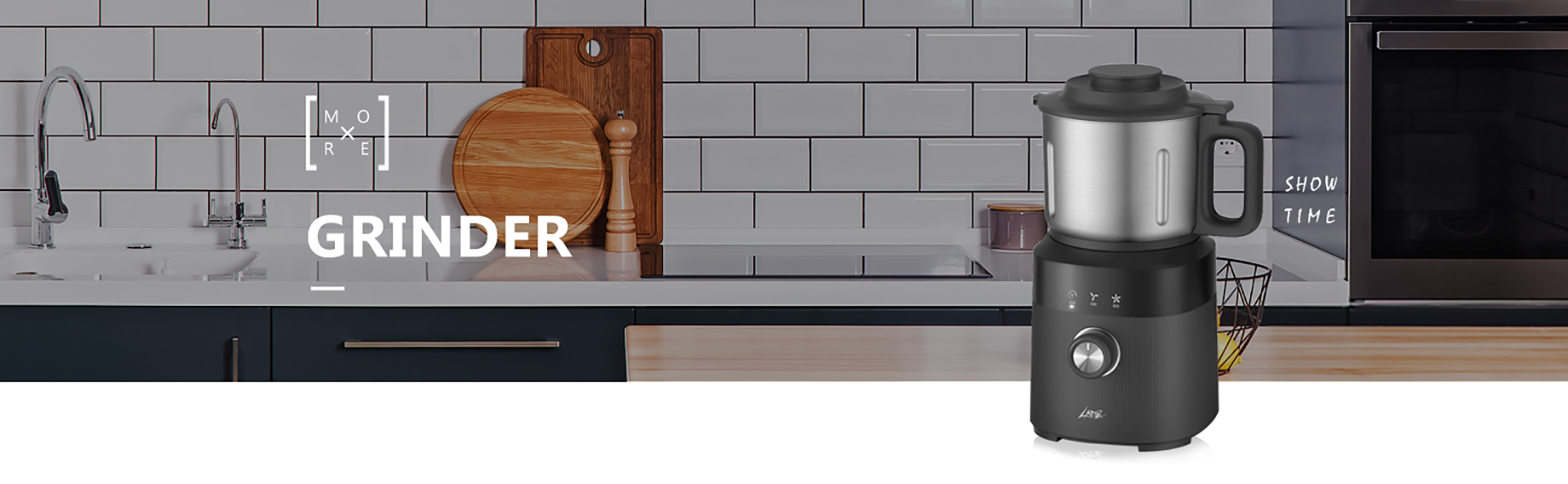
时间: 2025-04-02 09:29:03 来源:乐鱼官方下载
1965年末,罗瑞卿被诬害打倒了。这是一场犹如山崩地 裂的政治风暴。谢富治体现得反常活跃,亲身把握公安部的 “批罗奋斗”,亲身掌管党组扩展会,连续开了几十次。
在“联络实际”的幌子下,谢富治的锋芒首要指向徐子荣。 徐子荣是中心候补委员、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1927 年入党的老党员。同徐子荣一同被打倒的是狄飞,被谢定为罗 瑞卿的“死党”。狄飞是公安部党组成员、技能局长。
谢富治指挥、操作对罗瑞卿、徐子荣的批评奋斗,强逼 几十位部局两级干部和一些处长、科长、秘书等人人反省。
1966年4月间,谢富治要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奇清带 着我和党组成员、文保局长夏印到陆定一家里去“清收”文 件。谢宣告这是中心的决议。杨奇清带着咱们到了陆定一家 去搜索。这时,陆定一在外地,北京家里没有人。
这一反常行为,意图是搜索陆定一的“反党罪证”,用来证明陆定一 知晓和参与其夫人严蔚冰给叶群写匿名信的事。严蔚冰揭了 叶群的丑史。可是,没有查到任何“罪证”。陆定一不知道 严蔚冰的动作。
隔了一些天,4月下旬,谢富治又要我和国务院内务办 公室副主任、原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跟着他到彭真家里,也 是打着“清收”文件的旗帜。意图相同非常显露,是为了寻 找所谓“反党罪证”。
谢富治把“清收”的文件悉数放置在公安部南大楼一个 房间里,要我和严佑民担任,从公安部选几个人参与文件检 查。我早已察觉自己是不受谢富治信赖的人了。这时我选用让他人去管的方法来撂挑子。我和严佑民商定让素常较少触摸部领导层的消防局副局长肖孟来办理此事。“清收”的结 果相同是没有查出任何“反党罪证”。不久,谢富治宣告中止我的全部作业。
1966年5月,谢富治操作批斗徐子荣和狄飞的党组扩展 会敏捷升温。点名批评我和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凌云, 公安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尹肇之。
谢富治宣称公安部有一个以徐子荣为首的“地下黑公安 部”,同罗瑞卿保持着联络,进行直通罗瑞卿、对立谢富治 的活动。谢说“刘复之是地下黑公安部的参谋长”。我彻底靠边站了。
1966年5月开端,谢富治以罗瑞卿、徐子荣划线,点名批评简直全部部、局两级干部,不久,又扩展到被以为与彭、罗、徐和刘、凌、尹有牵连的人,把他们都打倒了。公 安部遭到这种“莫须有”罪名冲击的人有几十人。
一同,谢富治组成了一支造反派部队。他施行了“指挥 全部”。乱揪乱斗。徐子荣首战之地。下来便是我。给我开 过很屡次大、中、小批斗会、陪斗会。搞喷气式、罚跪、揪 头发、吐口水、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挂牌子游斗、游楼、 游街、监督劳作,等等。
在北京政法学院广场上批斗彭真、罗瑞卿的大会上,下 着霏霏小雨,几位年高德劭的老干部被拉上台陪斗。其中有 张鼎丞、杨秀峰这样的老前辈。在长长的陪斗部队中,我是 倒数第二个。排在最终的是尹肇之。徐子荣、凌云、汪金 祥、狄飞等人早被拘捕入狱。
1967年,在公安部大礼堂批斗徐子荣的大会上,我站在 台上左边陪斗行列的第一个。
徐子荣义正词严, 大义凛然,声响不大,但空气震动,我极为震慑和敬仰。徐子荣终被严酷摧残,惨死于狱中。这是其夫人孟松涛亲口告 诉我,她亲眼所见,人已断了气,才告诉她去看,躺在洋灰 地上,嘴上还有血渍。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批斗罗瑞卿的大会 上,声嘶力竭地呼叫有必要“砸烂公、检、法”,还宣称毛主 席说过好屡次。他经过公安部造反派编印的《公安红旗》和 其他造反小报,向全国广为传达,掀起“砸烂公、检、法” 的狂风恶浪。
谢富治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十七年公安作业的成果,全盘否定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污蔑公民公安机关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东西”,是“黑窝子”。
1966年9月,在“”高潮中,谢富治就把第四政委李震调到公安部掌管作业,担任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部长。
1968年头,将党组改为领导小组, 调曾威(工程兵政委)、赵动身(空八军副军长) 为部领导小组成员。
1967年2月11日,谢富治首要宣告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 军事控制;12月9日,宣告对全国公安机关实施军事控制。
1966年“”之初,我全家被从宿舍楼上赶到 楼下。1967年秋,被扫地出门(公安部),全家被撵到西单 灵境胡同合作巷一间堆煤的小屋里。 一段时刻,曾将红宇送 到空军学院王钊那里安身。每天,我骑自行车上公安部大院 里扫地。
1968年2月,勒令我到西郊中心政法干校公安部学 习班中的“黑帮队”承受批斗、专案检查,禁绝回家。在 “黑帮队”被专政了一年。我被称为队里的头号走资派,比 我资历老的几个副部长都被关进了监狱。
在批斗我时,杰出的是批“阶级奋斗熄灭论”,批“三 气”:怨气、傲气和不服气。他们在“挖地下黑公安部的爪 牙”中,陷害了一批人、株连了一批人。
在“黑帮队”期间,我将刚发下的薪酬放进挂在床头的挂 兜里。与我同住一个屋子的有四人。只在到食堂吃午饭的顷刻 功夫,薪酬不知去向,被偷走了。但专案组倒打一耙,极端主 观地诬害是我自己捣的鬼,是自己把钱扔到粪池里了。他们凭 这种极乖僻的推理,把墙外的粪池掏了个遍也没见到钞票的影 子。事隔好久今后,我听人们传出,薪酬是被一个造反派偷走 了,此人溜回老家去了。可是,专案组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弄清。
1969年3月初,专案组限令我在三天时刻,要举家搬家到黑 龙江集贤县笔架山公安部“五七”战校。谢富治和李震将这个劳 改农场改成“五七”战校,不叫干校而叫战校,宣称这是战役的 校园,要一辈子当农人。
18岁的大女儿红林已到内蒙插队。16岁的二女儿红燕也 于1968年末参与先遣队先期到达黑龙江这个农场六分场。我 同王岫联与14岁的儿子红森和8岁的小儿子红宇, 一同搬家。 但我不是下放,而是“放逐”,因而不能住在新家,而在农场 “小号”里控制了四个多月。
1969年3月6日,公安部1000多名干部、家族坐一列火 车从北京动身,前往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在硬座车厢里,人 流滚滚,红宇没有座位,就钻到我和王岫联的座位下面。
谢富治到了北京火车站,上车厢里欢迎下放人员,从我 面前走过期,旁若无人。但他走了几步忽然回来,假惺惺地同我握手,大声劝诫要“好好改造”。这是谢富治爱用的方法,把你摔得两脚朝天,再伸出手来表明拉一把。
3月8日,我住进农场关押特别监犯的“小号”里,不 让回到王岫联带着孩子们住的这个农场家里。我天天被指使 重劳作,给家族挑水、给场所泼水、拉大锯、刨冰冻羊圈、 铲地间苗、收割、打场、后半夜看场等。同我住一个炕上 的“黑帮”,有公安部干部尤文奎、白浩、赵荫农。还有受 检查的农场员工聂联增等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太行山上经受过各种劳作锻炼, 得益不浅。这一回,我的身体没有被搞垮,挺过来了。
大女儿红林1968年去了内蒙古阿巴嘎旗插队。二女儿 红燕在离咱们20多公里的六分场劳作,儿子红森在良种站 青年连劳作,小儿子红宇跟着岫联边劳作、边上学,得到 队上教师、公安部干部赵德珍的照顾。这回真是“扫地出 门”了。我时年52岁。
我能劳作、能吃饭、能睡觉。我默不做声,但达观世事。 我深信我国,深信毛主席,深信周总理不会把我这种人 丢掉的,深信真理在我手里。不论怎样折腾,我没有一点失望 越轨的想法。
虽然经常被专案组提审、挑刺、击打、批斗。我 多半是缄默沉静以对,不作答复。造反派质问:“你曾经长篇大论, 现在怎样不说话了?”
说什么好呢。我有时也“炒剩饭”,重 复“奉告”,照样挨批。专案组长说“要捞干的”。这是东北 口头语。我心想连汤带渣子都弄完了,还有什么干的?!
坦白说,我连一闪念也没有,我为何需求自杀?真是笑话。不 过我没有揭露跟他们对仗、讪笑。
在笔架山农场,我能吃完一个月48斤粮食定量,早五 两、午六两、晚五两。学习也专注致意,能熟背“老三篇”。 农场的大田里来了一辆新拖拉机,不少青年跑去观看。我心血来潮,从小号的工地里出来,跟着去看热烈。我也和年青 人一道爬上了拖斗。不料,司机忽然踩动油门,咯噔一声, 把我抛到空中又摔到地上,我戴着草帽有点像突如其来,幸 好没有跌落在小半尺高的玉米秆茬上,安全无恙。
在北京西郊干校集训时,有个病 号刘彦,也在受检查,但答应出去买点东西。在周末,她几 次悄然地给我留下点心。还有笔架山良种站农场员工、街坊老傅,半夜里杀了猪,第二天悄然奉告:有块肉扔到你房顶 上了。
我和王岫联带着红宇到笔架山场部医院给他看皮肤 病,正好碰上公安部处长、医师王亮。他给开了个处方笺: “刘洪宇同志因患病需求鸡蛋配药,请售予三斤,此致敬礼, 中医王亮,12月19日。”(1969年)
咱们领受了王亮的厚意 厚谊,但没有敢去买鸡蛋,防止招惹是非。但把便条留下 了。那时敢给我开出三斤鸡蛋的便条,友情比黄金还宝贵。
大女儿红林随一批同学跑到内蒙古插队。还算碰巧了, 在那里得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邓存伦和副政委张南 生的协助。
邓存伦是我在延安中心党校的同学。张南生是老 上级。红燕和红森1970年末从笔架山跑出去从戎,路过北 京,无家可归,也得到张南生、林纫篱配偶的照顾,过夜; 到福州后,由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和福建省委副书记卓雄 安排到部队执役。
其时,还曾有些忧虑孩子会被造反派揪回 来。但不久传出,毛主席说,走后门从戎也是革新的。专案 组没有追查。在我身陷窘境时,朋友伸手帮助,让我感到难 忘的温暖。
王亮同志是中医,红宇在小学被感染肝炎,一同发现了 好几个孩子抱病。这是1969年冬,咱们是专政对象,孩子病 了,医师不敢开药。
我记住我带他去佳木斯医院验血证明肝 病,我都要急死了。在佳木斯住了一个晚上,我回到笔架山 农场,其时医院医师只说让吃葡萄糖,打球蛋白,他那儿还 没有,我四处求人。还好,鲁毅搞了几盒,李黎搞了几盒, 刚好刘复之出来作业,在上海搞了几盒,部里去的大夫说打 一阶段就行了。
“三高”我想尽了方法。最终球蛋白太多了, 剩余的又不敢送人,这个状况,没被整过的人欠好体会到。 我叫刘红宇喝了,现在听了好笑,其时可紧张了,宇儿没留 下后遗症。
这个三斤鸡蛋票,没敢去买,也不想去买,其时 发薪酬,有钱,不去请假买鸡蛋,所以这个票就留下来了。 惋惜现在的孙子们不明白。
版权所有 © 2020 乐鱼网页版-登录页面 技术支持:网站地图